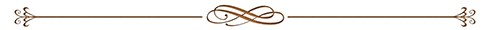柏林,我在这里受伤也在这里治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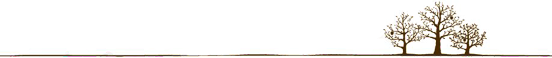
在巴塞罗那含蓄的微凉里接过 GORUCK Stealth、Prime Challenge、OCF 三块纪念布贴之后,换上雪白的冬毛,走进苏黎世的冬天。
苏黎世的冬天阴冷而潮湿,与西班牙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截然不同。尽管走出机场的一刻颇使人领会现实扑面的残酷,但回到十一月该有的样子,我也像在此安家的冬季精灵一般,拥着熟悉的安全感,任凭记忆在脑海中轮回。
按理说,我应当因人生第一次打通 GORUCK 全套而无比自豪,可是强烈的思绪不由分说,将我时时拉回一年前的柏林——那直到今日即便细节都已模糊,其意义也难忘怀的,GORUCK 征程的起点。
哦,没有人记得,一年前,在我的人生最艰难的时候,这座城市如何赐我浴火重生的痛楚和幸福。


报名柏林 GORUCK 的时候还没有 CSAE 的存在,但 ++ 的特长和你今天所知的完全一样。我和 Neo 和隋文帝就是这样如你所知地上了车——哪怕彼时 Stealth 和 Urban(后来被 Prime Challenge 取代)每场都要百余欧元票价。
直到活动开始的两个月,我始终怀着畏惧和勇敢交织的心情。对即将到来的一无所知,不知从何准备,又觉得如何准备都不够。然而在极不安的境况下仍选择背水一战,这大概是我——如果说——取得任何成功所依靠的秘诀吧。
我们开始互相监督着锻炼。我和 ++、Neo 约定,每周步数最少的一个人要给另外两人发红包。
那时我大概正处于难熬的抑郁中吧。我不愿回想那些日子的细节。我只知道,只能靠提出这个方案来逼迫自己行动。我别无他法。
依稀记得,当我一次次麻木地交钱出去,++ 说:「设立这个机制,本来就是为了督促你们出门,如果你们像这样甘愿认输,那这个机制还有什么意义呢?」
我告诉自己要坚持。我购置装备,练习长跑,游泳,俯卧撑,负重徒步。两个月过去,++ 毫无悬念地收了最多的红包,而我拼尽全力,仅仅做到收支平衡罢了。
转眼到了 10 月 29 日,NL1331 的车开到苏黎世。当 Hilda 听到我报名了三场 GORUCK 的消息,她的嘴张得老大,随后对身边的绿军 POC 说:「今天的小姑娘们,都有你无法想象的勇气。」
我真的以为凭这份勇气可以无往不利。


11 月 3 日早上,我感到疲倦异常,在床上无数遍催促自己睁开眼,而飞往柏林的航班已离开苏黎世了。
「也许这就是鸮吧。」群里的人们这样说。
真没用。我骂着自己,去机场改签了下午的飞机,随后发现这份异常疲倦的缘由,才是真正令我恐慌到绝望的——
生理期到了。
我无法思考。百万张退堂鼓在脑海中轰鸣,Hilda 的话此刻像是充满了嘲讽。
痛。到了柏林,我万般不顾,爬上施普雷河船上的小床,在渐暗的天光里朦胧睡去。
晚上八点多,++ 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躺在床上犹豫不决。没吃晚饭,但因睡了一觉而不太觉得腹痛。++ 充满活力的样子使人莫名振奋,他问我好了没有,我看着他,脱口的话未经思考就变成了:「我好了。」
我还是如此渴望背水一战。

早年的 Stealth 强度比如今高出一倍不止。单是热身就从晚上九点进行到十一点。项目包含:跑圈,快速清空及重装背包,蹲起,马步,俯卧撑,熊爬,踢腿,前滚翻,折返跑……
这两小时的记忆于我,是公园上空阴森的夜雾,夜雾中闪烁的头灯,头灯下湿漉漉的草叶,草叶间沾满泥渍的双手和不绝的喘息。再多的文字便无用了。

夜里十一点到次日上午八点半,是四十公里负重徒步外加若干项比赛。其中一项是找出双方阵营等级最低者,结束时比较两人 AP 增量,增量多者阵营获胜。能在这种项目被选出来的,自然只有我,10 级的我。
我的膝盖大约受伤在凌晨零点到一点之间。
因从出发开始,我便一刻未停,在整个蓝军队伍之间折返奔跑,以抢到更多 AP. 队友们都很配合,沿途白 po 会留给我占领。
行进至东边画廊,我被要求和另两名队友离开队伍去做多重。为争取时间,我一路奔跑,而体力已下降,跑姿愈发扭曲,难以控制腿部肌肉。大约是被井盖之类硌得失去了平衡吧,我扭伤了左膝。
做完多重,即刻由东边画廊跑去电视塔下和大部队会合,前往柏林大教堂。
我和一名女伴去找厕所。我对她说:「请帮我拿一下包,我要拿……点儿东西。」
她说:「我知道。」
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那一刻会给我无与伦比的感动。

凌晨一点半,由大教堂出发。
一点五十五,查理检查站。
两点十五,勃兰登堡门。
两点四十五,胜利纪念柱。
三点,勃兰登堡门。休息,进行另外的比赛。
四点半,返回大教堂附近,之后重复上述路线。
起初我咬牙坚持跑步;然后我把背包给别人,坚持跑步;然后我只能连走带跑;凌晨五点半,最后一次返回勃兰登堡门的时候,我几乎无法站立。膝关节深处传来的刺痛,每一下都使我全身冷汗。
「你还能走吗?」
「我不能了。」
我们必须在六点之前到达。一名队友背起我的包,另一名队友背起我,全力奔跑。
「我说,你真的很轻哎!」
可他很快也虚脱,请求我下地。我扶着他小跑了一段,他再次用力背起我。
黎明将至。


最后的行程是由勃兰登堡门返回东边 Arena. 七公里。
东方由微亮到灰蓝,再由灰蓝到橙红。我们一路向东,始终面向天空中最绚烂的色彩。街上车声渐起,房屋、树木都慢慢浮现了颜色。柏林晚秋的周六清晨,一如既往地清冷而萧索。
整个城市唯独和这份萧索格格不入的,怕是只有菩提树下大街上四肢着地窸窸窣窣爬行的队伍了。偶尔有人站起身,便听得旁边高个子教官的厉声呵斥。
爬完之后是驮人,两个驮一个,快速前进。我完全想不到保持手臂伸开挂在别人肩上有多么困难,不知两名队友是否也和我一样。然而,只要三个人还勉强挂在一起,无论如何狼狈,跑完拉倒。
太阳升起来,我们在路边草坪上进行了最后一项体能竞赛。双方壮士围成一圈,将包举过头顶。
晨曦里加油声此起彼伏,而「Resistance」这个词汇本身铿锵有力的音节和特别的含义,在此类耐力竞赛中显得比「Enlightened」更能凝聚团队的力量。


共同参加过 GORUCK Stealth 的人是很容易成为患难之交的。尚且不提绿军 ++ 一脸嫌弃地走过来递给我汉堡的恩情,蓝军波兰球姑娘娜塔什卡(@Nataszka1975)与我相识于 Stealth,随后亦成了互相扶持的好伙伴。
我俩边走边聊,滔滔不绝,引来暴脾气红发妹卡西雅(@Orant)无数次怒斥:「别说了赶紧走!」于今想来甚是惭愧,因在巴塞罗那也遇到了只顾说话而耽误行进的友军,在团队中着实有些不负责任。
但是有波兰球在身旁,带来的欢笑足以支撑一双伤腿向前迈进。一路「kurwa、kurwa」的,不觉天明。
接近终点的那段路,波兰球将手伸给我,扶着我走。我们十指相扣。我们笑得那么真挚。



不出所料,我的 AP 比拼输给了绿军。而出乎我意料的是,在终点进行的人体 glyph 比赛,使得这副残躯最终有了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一搏。
每方要求选出六名画图能手和一名指挥,我自告奋勇瘸着腿走上前去。规则很简单,教官依次说出 glyph 名称,最快拼出的一方获胜。
蓝军的表现有些过分优异了:教官刚说出单词,几个人就默契就位躺下,完全不用指挥操心。其中当然包括我,我浑身上下仅剩的本事只有记 glyph 和卧倒,能这样帮助蓝军取胜,余热也算没白发挥。
朝阳下的布贴是金色的。我觉得值得。


回到旅店,只见膝盖肿得馒头般浑圆锃亮,殊不知那就是此后一年的病根。我无奈放弃了当天的 Urban,只参加了周日的 OCF.
当然,也如你今日所知,在柏林的这个周末是未来许许多多故事的伏笔。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biocard,第一次和海王睡上下铺(哦,她在上面),第一次见到了我日后那样深爱与不舍的 CSAE 的大家。
这是我的 Ingress 史上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。虽然不像苏黎世的春节般「天时地利」,但「人和」带给我的满溢幸福甚至可以战胜一身伤痛。
Get up. Get out. Get strong. Get social. It's JUST time to move.


当一年后终于在巴塞罗那完成 GORUCK 全套的那一刻,我竟觉得毫无压力。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:气候适宜,着装减轻;Stealth 难度下降……但不可否认的是,我因经历过「真正的」Stealth,对自身潜能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原有的水平。
站在今天回顾过去这一年,我敢说我始终不曾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与伤病的不懈抗争。我敢说我为自己取得的进步而骄傲。
如今我已脱胎换骨,迎接未来的崭新图景,而这一切,我相信是起源于柏林,起源于 2017 年晚秋的那个周末。